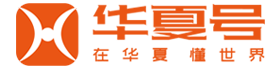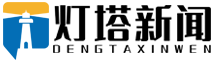以诗意书写生活
——读艾华林诗集《当我卑微无名时》
■ 陈婉红(浙江)
几年前,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”这句话流传甚广,寄托了无数人的美好理想与向往。生活是苦乐共存的,在眼前的磨难与艰辛里,诗和远方是自己创造的,当我读艾华林的诗歌时,我如是想。命运,它会赋予每个人不同的生存哲学和人生意义。
艾华林曾经说过,“生活并不只有苦难和泪水,还有阳光和微笑,这取决于我们面对生活的态度和勇气,视线不同,风景自然迥异。”他完全颠覆了我对打工诗人的认识,他将艰辛的打工生活与古典诗歌浪漫而诗意的血脉传统打通了。欧阳白教授对他评价有言“读他的诗歌时时能读出正能量,读出宽厚的心境和宽容的品格。”这是与印象中的“我们沿着铁轨奔跑/进入一个个名叫城市的地方/出卖青春,出卖劳动力/卖来卖去,最后发现身上仅剩一声咳嗽/一根没人要的骨头”(《失眠》)这类的打工诗歌,截然不同的。
艾华林的诗,如他在《灯笼》中所描述的,“柔仁的心,韧性的骨骼”,刚柔并济,有无相生,祈愿、恬淡、唯美、顽强、坚韧……是他的诗歌色彩。
结合艾华林的人生经历,他曾经在武警部队锻造,因此他的本质性带着坚强刚毅,但在努力生活、寻找梦中桃花源的过程中,他携有最柔情细腻的情感,含蓄出了朵朵生活里的诗意的花。
诗人的成长经历、修为体悟、艺术涵养以及内在气质都是构成作品风格气度的决定性因素,一个人的所思所想都会嵌在他的文字里。雾里看花、流水潺潺、油纸伞、旗袍、春雨、垂柳、青山、月色、星空、云海……种种静谧细腻浩瀚的意象经常出现在他的诗稿里。他的诗集中,不乏有外乡打工、为生计忙活的生存境况型的创作,但更多的,是乡愁,是人生追求,是生活所思,他的写作视域逐步扩张不再受打工诗的标签所限,不再受地域时空限制,诗歌,愈发纯粹。
纯粹的细腻又带出艾华林诗歌的另一个特点——画面感很强。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物象,在阅读诗歌时,我的眼前总是能够浮现出他所描绘的画面,也能体会到其中的意境。如《西塘如湖》中“春水一汪,荷塘半亩,垂柳三尺/七八个采莲女,泊船在水中央”,几个数词,几个搭配的量词,眼前就有了生动的西塘景象与采莲画面;又如《梦里水乡》中“一把油纸伞,一袭青釉的旗袍,信步款款/走过曲榭廊桥,就演出了唐诗的韵味”,仿佛就看见了江南女子悠悠然地散步长廊,与天青色的幕布融为一体。这些有质感的语言串起了画面,把读者引入绝佳的“境”。恰如《走读河伯岭》“站在河伯岭的山头/看鸟雀成群的飞/看流云慢悠地远去/再看看白云下面的自己/我突然觉得,我的天空好辽阔啊”,以意象为铺垫,一步一步带着我们走向广阔之境。以“境”而生,文字之外寄情其中,读者又能从贴近现实生活的诗歌里感受到众多深刻的、纯粹的、前瞻的东西,婉转流畅不失深意。
在阅读艾华林这些诗的过程中,我又感受到了若隐若现的熟悉感。他写现代诗,化用了许多传统诗词,熟悉戴望舒、海子、洛夫、余光中等现代诗人的艺术心法。我想,打工诗人的画风,不论是“望文生义”式的理解也好,还是他人有之的刻板印象也好,给人的感觉是现代的,是车间,是工厂,是螺丝,是房贷,是苦难……但是艾华林的诗歌里,是古典。张继、李白、王维、崔颢等都出现在他的诗歌里,枫桥、乌啼、南归、黄鹤楼……有形无形意皆在,这与他“做诗人梦,读了很多古诗”脱不开关系,他将自己能读到的古诗抄在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上,放牛、砍柴、喂猪都带着,山间林里都是他读书的身影,正是有这样的源头滋补着,所以艾华林能写出独特一份的打工派诗歌,杂糅了现代与古典,别有一派风味。“淡蓝色的天空下/空悠悠的白云/载着诗人千年的梦/跑过连绵起伏的高山/黄鹤踪影全无/乡关无处可寻——”。此地没有“黄鹤楼”,此地没有“鹦鹉洲”,此地没有“汉阳树”;“但此刻,在土司王朝的旧址上/在日暮的余光中/我仍有崔颢一样的乡愁”。(艾华林《五一登程子山》)含蓄蕴藉的艺术手法描摹的诗行字面下,包藏了汪洋恣肆的情感。
张爱玲曾说过,“我们高举双手,不是为了摘取星辰,是为了保持一种向上的姿势。”艾华林就是这样。“就算诗树不会开花/我也会保持应有的期待/让生命悄然前行”,是他写的《信念》一诗,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他的生命节奏。
艾华林的诗歌,大多都是柔和坚韧又积极乐观的。如《珍珠》“醒了。我像一个虔诚的信徒/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跪下去/无视于上天的垂询和怜悯”;如《信念》“假如世界没有了光明/我愿意优雅地沉沦/像雪花融入大地/像羽毛飞向天空”;即使也有书写生命艰苦的笔触,足够沉重但不沉郁,总是带着一股淡淡的忧伤,如《这些年》“第一次被老板炒鱿鱼时/我听到了灵魂撕裂的声音/春风吹,柳枝摇/我感觉村头的槐花孤独地开了。”春风柳枝象征生机,与“槐花孤独地开了”置于一篇里,不显得奇诡,春风的略微生气冲淡了家乡槐花独开营造的伤感。“在一个雨后的黄昏/我才意识到心中若有若无的悲伤”以景带情,引出这股淡淡的似有若无的感伤,悲却不至于痛。
也很少见打工诗人写出如此佛性的诗歌。参禅悟道是艾华林的又一人生轨迹,他会写“把自己隐起来,不是想逃避什么/沉睡深乡,是想把内心的种子焐熟/从淤泥里出来,到娉婷尘世/她不染风尘,不着风霜/一旦开莲,便参透了人生”(《睡莲》);“一开始,他便被黑夜所牵引/在寂寥的时光里,他一往无前/走向虚无,黑夜之光,照着他/这是一个怀抱莲花的人/他内心干净、纯洁,像一只野性/未泯的小兽,时刻准备着突破/世俗的樊篱”(《向死而生》),这是禅道造景,虚实相生,果真是佛光普照,融融泄泄的一番姿态。“在心里点一盏灯,远离虚无,远离颠倒梦想/心无挂碍,就不会被虚无所缚/我记得,菩萨是这样开示我们的/父亲也是这样敲打我们的”(《给父亲》);“黄昏,去神滩/是想碰碰那位假扮渔夫的神仙/不知他倒驾慈航的般若船/能否度我今生的苦厄”(《神滩晚渡》),此类便是更为直接地点出佛教中的神祇,依托佛理,抒发自己的困惑。在他的《岳平云顶》中,“去上庵殿,要把门拴上/换一副心肠活着/居庙堂,不诵经,不作画/一卷诗书,就坐一上午/倦了,乏了,舀一勺清凉、洗心/革面,镇住孤独/一碗青茶,就可以治愈心伤/一笔,写出撇捺人生/长短,不悔一字/高低,不悔一字”简短的词句、爽快的节奏、禅味的意象,就是他尤为出彩的表达了。
艾华林始终相信着,举头三尺有神灵,敬天爱人是他一生的信仰,信佛信命,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,顺其自然是他奉行一辈子的准则,所以他能写出这样一册诗集便不觉得奇怪。相信天命的人自会懂他,他道出了一种生命的智慧与哲学,大千世界变化莫测,命中注定顺应自然何尝不是一种逃离苦难的精神支柱,如若不是这样的精神续脉,也难以得见艾华林中“当我卑微无名时/我要好好地爱自己”“当我卑微无名时/我要爱身边的每一个人”,如果束缚在尘网,那就终究无法洒脱。
《我曾这样卑微地活着》“就这样卑微地活着/活成一棵挺拔的青松/不出摊时,就在家里/安静地读几首诗,码几行字/像古代流放的诗人/卑微地活着/活成一株清雅的荷/每当眼泪要掉下来时/就把头抬起来/看看那些干净又慈悲的云/我就觉得很幸福”;《活在这珍贵的人间》“活在这珍贵的人间/我们太需要爱了”。简单朴实的话语,细数一辈子的经历,描绘眼下的生活情景,道出了生命的真谛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,活在人间里的意义是什么,支撑的动力是什么。艾华林告诉了我们答案,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,艾华林说出来了,我们因爱活着,以爱活着。
读完《当我卑微无名时》,就会感受到,艾华林的诗歌,言之有物,读之有情,兴起而作,语罢绕梁。读他的诗歌,可以看到那一幅幅他眼前见到的画面,可以听到他口中或者心中的震耳欲聋的发问,也可以共鸣到他脑海中所思所虑,虽然是打工诗人一派,但却阐述了众多普普通通人的心声,谁都又何尝不是无法圆满地活在世间,谁又不是要继续乐观豁达清醒地活在人间呢。当一个人看过足够多的世界,他就会喟然世界何其之大,人生何其之渺小,艾华林生于山川之间的湘地,去过东北入伍,在繁华的深圳谋生,走过江南的西塘、周庄,跨过中原的开封、陈桥,隐居云之南的芷村,见过古老蹉跎过现代,遨游得足够广,经历得足够丰,静坐得足够久,慢慢地“神就会上身”“我就会想明白一些无常的事情”(《参禅九华山》)。我们应当如他一般清醒澄澈,苦难是人生中难以避免的,是佛说的坎,该要自渡还且渡,又莫不能失了生活心。
当还以诗意书写生活,这并不意味着一股脑地追求诗性,如果可以,多走走世界,既用眼睛看,也用心灵看,走的多了,让表皮与骨骼越发的坚韧,让思想与内心越发的仁柔,从而获得一种包容万物的境界,也是佛性的境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