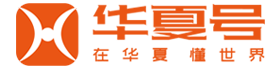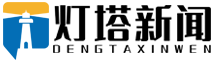发小二雷
■齐大志(北京)
雨季不下雨,黄土地干裂的口子,让人想起嗷嗷待哺的黄嘴燕雀。
“管子怕轧吗?”
“不怕,熟塑料的。”我正在浇菜,看见一个戴墨镜的人,骑着电动三轮车,停在我家门口,等待放行指令。我补充一句:“让开墙根儿过,别把水管接口轧坏。”
话音刚落,就听到一声闷响,接着就是哗哗的流水声。循声跑出菜园,我看到三轮车侧翻,骑车人正挣扎着从驾驶位往外爬,墨镜被甩出老远。
“二雷,是你?多年没见,发小我都快认不出了。”我帮着二雷脱身。
“你不记得我,我可忘不了你。”二雷龇牙咧嘴地斜我一眼。
“伤着没?”
“没事。本想拉一罐水去浇菜,没想到这车……偏偏在你门口翻个儿了。”
村街铺设的污水管道刚填完新土,地软乎乎的。二雷的后车轱辘,一个轧在街边的水泥路,一个陷入街中央的囊土里,车身失衡引发侧翻。
我帮二雷扶起车,想把车头扭正,不小心触碰到车的动力把,车头蹭地撞到菜园的铁丝围栏。我的右手划出了血。感觉没有伤筋动骨,我用左手捂住伤口,没吱声。
二雷从车后绕到车头,也不知他看没看见我受伤。总之,他一句客气话都没说,骑上车就走了。
我心说,好发小的关系一点儿不假。但,就冲我上赶着的一阵忙碌,也该说句暖心话啊。这人之常情的事,我却没等来。
看着二雷的背影,我不免有些郁闷。工夫不大,我听到吱嘎一声,见二雷下车了,急急地朝我走来。这出乎我的意料:心里猜测,一定是二雷感觉就这么走了不合适,回来跟我补说几句暖心话。可二雷走出十几步,又停住了,抬手在嘴前团个喇叭筒,朝我大喊:“记住,往后别叫我二雷,我叫雷庆德,不再改名!”
二雷雷霆般地喊话,把我唤醒了……
刚一出生,二雷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叫雷震宇。上小学的时候,同学和村里的伙伴儿,总爱拿他的名字打趣:“今天是大雨还是小雨啊?”
“不是大雨,也不是小雨,而是雷阵雨”。
每当这一问一答的话灌进耳鼓,二雷都会攥紧拳头,瞪起愤怒的眼睛。
毕竟是同村的伙伴儿,后来我出了一个点子:“你们说得都不对,雷震宇过年最喜欢看大人放二踢脚。他说二踢脚一响,就像天空打了两个响雷,两个响雷,不就是二雷嘛。所以,往后咱就叫他‘二雷’吧!”
二雷听了,没说啥,只是嘿嘿笑。打那儿,“二雷”这个外号就在课堂外叫开了。上中学时候,二雷自己曾改过几次名,仅我记住的,就有“雷庆轩”“雷庆余”。而且,他把名字改过来,相隔时日不多,往往又改回去,弄得老师也不知道咋称呼他好了。
我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工作,偶尔回故里小住几日,也没跟二雷见过面。只听说他在外面打短工,日子过得还算不错。至于“雷庆德”这名字是啥时候定下来的,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……
带着手伤继续浇菜的时候,我反思:就算我没有一丝调侃二雷的本意,可将眼下已经六十岁的雷庆德还叫“二雷”,确实不妥。雷庆德比我小两个月,在村里同辈分,甭管他现在到底叫啥名,我起码可以称呼他“老雷”“雷弟”“老弟”。
正想着,听到哐当一声,接着就是带着伤感的自我埋怨:“我咋这么没记性呀,不到半个钟头,就在一个地方摔俩跟头。老了、真是老糊涂……”
我跑出菜园,踩进泥坑,边扶庆德,边喊“老弟”。
庆德两手紧紧搂住我的肩膀,爽声答应。泥水把我俩融在一起。
站稳身子,庆德像是想起了啥,赶紧打开车座厢,从里面掏出个塑料包,递到我眼前:“刚从卫生所给你拿的外伤药……”
我眼圈儿发热,一时无语。
“眼下,我想求老哥一件事。”庆德的表情很是真诚,“往后,你还是叫我二雷吧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