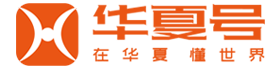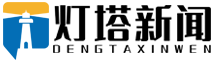我的母亲
■姚志顺(江苏)
那天上午,阴沉沉的空中裹满了雨水,像要哭。去母亲的坟上烧过纸钱,叩过头后,我便回到老屋——母亲在世时住的房间。恍惚间,母亲的音容笑貌和她忙碌的身影,犹在眼前,历历在目。
小时候,大约七八岁的样子,疾病一直形影不离地缠着我。母亲虽有忙不完的农活和家务,还是尽可能地挤出时间陪伴我。很难想象,若无母亲的陪护,那段日子我怎么能挺过来?或许早已死去了吧!每想起那疾病缠身的几年,我总这么坚定地认为。
那时,每到夏季,我就打摆子(疟疾),忽冷忽热,高烧不退,满嘴火泡又不想吃饭,人瘦得皮包骨头。因为家里很贫穷,买不起药更看不了医生。母亲就到处去寻求民间偏方,听人说何首乌叶子下面条拌蒜吃可医此病,她便顶着烈日,在本可以,也是唯一得以休息的中午去找何首乌叶子,洗净切碎,从邻家借来面粉,不一会,香喷喷的手擀面端到我面前。我虽饿得要命,却毫无半点胃口和食欲。看我不吃,母亲抚着骨瘦如柴的我,又亲又哄。看母亲着急的满眼泪水,我会勉强吃一、二口,母亲便会高兴地连说:能干,真乖!没有对症的药治,我常常被烧得不省人事、胡言乱语。每每此时,母亲急得失声痛哭,手忙脚乱地拿凉毛巾擦拭我的脑门和胸口。我一次次模模糊糊地醒过来后,母亲都是满面泪水,抱紧闯过鬼门关的我,喃喃道:我这二儿子脑子不会烧坏吧……不会傻了吧……母亲因担心经常高烧的我,被烧成痴呆,会哽咽着念叨好久、好久……
夏日的晚上,酷热难当。家里没蚊帐和风扇,就连蚊香也买不起。母亲早早扛上门板和芦蓆,到谷场上选一块干净的地方铺开。我们兄弟几个一字排开,挨头睡下,在母亲蒲扇轻摇的微风中甜美睡去。无论我夜里醒来几次,总能看到睡在我旁边的母亲,手中的蒲扇在机械又规律地摆动着。我的母亲,就这样整夜似睡非睡地照看着我们,为了她的孩子们不被蚊虫叮咬、睡得好,她的整个夏季也睡不上一个完整觉。为照顾我这病秧子,母亲每到夏日结束,也如大病一场,会更加消瘦。
这样持续三个年头。后来母亲不知听谁说有个偏方包治我的病,便步行往返几十里路求了来单方。我的病就这样在母亲无微不至的关爱中,渐渐地好起来。
走出母亲的房间时,已是黄昏,雨后的夕阳,惆怅着把最后的余晖洒满老屋的小院。院子里的猪圈和鸡窝还在,只是不见了鸡和猪的影子,不见了母亲唤它们吃食的声音;大水缸和小石磨也在,只是不再有母亲躬身碾磨和挑水的身影;连母亲种于东墙角的野乔梅(没经过培育的蔷薇)也还生机勃勃地开放着。没有了母亲的小院,冷冷清清。没有了母亲后,老家从此变成了故乡。没有了母亲的我只能泪眼向天,祈愿我的母亲于天上不再辛劳、幸福安康!